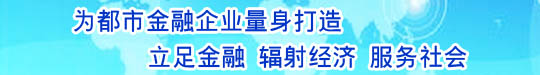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进入无垠广袤的人生
24载,8000多个日夜,为了追逐梦想,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、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,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。
9月25日,“天眼”落成启用一周年。可在10天前,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:“天眼”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,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。
“天眼”之难
24年前,日本东京,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。科学家们提出,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,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,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。
南仁东坐不住了,一把推开同事房间的门:我们也建一个吧!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态。
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,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。可他说:我得回国。
选址,论证,立项,建设。哪一步都不易。有人告诉他,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,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“天眼”台址,南仁东跳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。
1994年到2005年,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。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,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,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挪过去。
“天眼”之艰,不只有选址。这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,天文学、力学、机械、结构、电子学、测量与控制、岩土……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,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
“天眼”之难,还有工程预算。有那么几年时间,南仁东成了一名“推销员”,大会小会、中国外国,逢人就推销“天眼”项目。
审核“天眼”方案时,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,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,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、反复计算。即使到了70岁,他还在往工地上跑。
中国为什么不能做
“天眼”曾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。口径500米的中国“天眼”,在不少人看来,是“空中楼阁”。
中国为什么不能做?南仁东骨子里不服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开会时,他就会用一口不算地道的英语跟欧美同行争辩,从天文专业到国际形势,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,完了又搂着肩膀一块儿去喝啤酒。
“天眼”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,每个领域,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,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。没有哪个环节能“忽悠”他。这位“首席科学家”“总工程师”,同样也是一个“战术型的老工人”。每个细节,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,如果没有解决,就一直盯着,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。
工程伊始,要建一个水窖。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,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。施工方惊讶极了: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?
外人送他的天才“帽子”,南仁东敬谢不敏。他有一次跟“天眼”工程副经理张蜀新说:“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?其实我每天都在学。”
性格里的“野劲”
南仁东的性格里有股子“野劲”,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。
2014年,“天眼”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,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,亲自进行“小飞人”载人试验。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,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。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,全程需手动操作,稍有不慎,就有可能摔下来。
如果把创造的冲动和探索的欲望比作“野”,南仁东无疑是“野”的。在他看来,“天眼”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,而是“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”。
南仁东其实打小就“野”。他是学霸,当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,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。工作10年后,因为喜欢仰望苍穹,就“率性”报考了中科院读研究生,从此在天文领域“一发不可收拾”。
不是院士,也没拿过什么大奖,但南仁东把一切看淡。一如病逝后,他的家属给国家天文台转达的他的遗愿:丧事从简,不举行追悼仪式。
“天眼”,就是他留下的遗产。还有几句诗,他写给自己,和这个世界:“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,召唤我们踏过平庸,进入它无垠的广袤。”陈芳王丽等
9月25日,“天眼”落成启用一周年。可在10天前,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:“天眼”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,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。
“天眼”之难
24年前,日本东京,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。科学家们提出,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,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,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。
南仁东坐不住了,一把推开同事房间的门:我们也建一个吧!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态。
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,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。可他说:我得回国。
选址,论证,立项,建设。哪一步都不易。有人告诉他,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,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“天眼”台址,南仁东跳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。
1994年到2005年,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。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,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,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,深一脚、浅一脚地挪过去。
“天眼”之艰,不只有选址。这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,天文学、力学、机械、结构、电子学、测量与控制、岩土……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,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
“天眼”之难,还有工程预算。有那么几年时间,南仁东成了一名“推销员”,大会小会、中国外国,逢人就推销“天眼”项目。
审核“天眼”方案时,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,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,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、反复计算。即使到了70岁,他还在往工地上跑。
中国为什么不能做
“天眼”曾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。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。口径500米的中国“天眼”,在不少人看来,是“空中楼阁”。
中国为什么不能做?南仁东骨子里不服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开会时,他就会用一口不算地道的英语跟欧美同行争辩,从天文专业到国际形势,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,完了又搂着肩膀一块儿去喝啤酒。
“天眼”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,每个领域,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,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。没有哪个环节能“忽悠”他。这位“首席科学家”“总工程师”,同样也是一个“战术型的老工人”。每个细节,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,如果没有解决,就一直盯着,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。
工程伊始,要建一个水窖。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,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。施工方惊讶极了: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?
外人送他的天才“帽子”,南仁东敬谢不敏。他有一次跟“天眼”工程副经理张蜀新说:“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?其实我每天都在学。”
性格里的“野劲”
南仁东的性格里有股子“野劲”,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。
2014年,“天眼”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,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,亲自进行“小飞人”载人试验。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,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。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,全程需手动操作,稍有不慎,就有可能摔下来。
如果把创造的冲动和探索的欲望比作“野”,南仁东无疑是“野”的。在他看来,“天眼”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,而是“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”。
南仁东其实打小就“野”。他是学霸,当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,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。工作10年后,因为喜欢仰望苍穹,就“率性”报考了中科院读研究生,从此在天文领域“一发不可收拾”。
不是院士,也没拿过什么大奖,但南仁东把一切看淡。一如病逝后,他的家属给国家天文台转达的他的遗愿:丧事从简,不举行追悼仪式。
“天眼”,就是他留下的遗产。还有几句诗,他写给自己,和这个世界:“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,召唤我们踏过平庸,进入它无垠的广袤。”陈芳王丽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