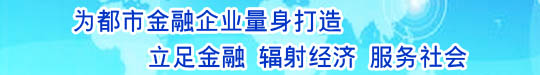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打火记
“舒家垄发大火了,大家快去打火(鄂南那一带习惯将灭火称作打火)呀……”我们坐在黑桥小学的教室里,正聚精会神地听语文老师炳奇用一口田心话朗读着课文。只听见学校的工友光明伯(他好像就是舒家垄人)在校园里扯着破嗓子急促地吆喝着。顿时,我们的心飞了出去,哪还能专心听讲啊?齐刷刷地都把头别向舒家垄方向,但隔着窗户上的毛玻璃,外面什么也看不见。班里有几个同学是舒家垄的,梦林家也是。他们听到光明伯的吆喝后就更是揪心,心像猫爪一样抓,不知是不是自己家发火了?他们急着站起来,没和老师打招呼就往外跑。老师也没得法,“火灾就是命令”,尤其是在乡下,只得看着学生们冲出教室,随即,自己也出了门。操场上已全站满了师生,望着舒家垄的方向,七嘴八舌,指指点点。校长带了几名壮硕的年轻老师还有光明伯,和高年级的学生们已经端着洗脸盆和提水桶奔跑着,一窝蜂地到舒家垄打火去。
崇阳多山,俗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东北部的田心黑桥的两山之间,有一垄平畴,除了弯弯曲曲的田塍围着的水田外,还有一处像浮在田间的岛屿一样的屋堂,和众多的鄂南民居一样,也是屋连着屋,廊连着廊,甬道连着甬道,天井连着天井;而屋里的内饰多为木制品,包括门板、桌椅、木柜、雕花窗和床;只有高高的山墙,翘出飞檐,隔着每片屋宇,也是一道防火墙。屋宇上,鱼鳞般的黑瓦,一摞一摞地排列,瓦沟深幽,长满青苔,透着沧桑。因屋堂的人大多姓舒,便有了舒家垄这个名称。舒家垄离我们读书的黑桥小学不远,十几分钟就能到。下课后,站到操场上,一眼就能望到舒家垄的俨然房舍和在农田里耕作的农人。
火苗,隔老远就能看到像蛇信子一般的火苗在往上蹿。紧接着是巨大的浓烟,像烽火台的狼烟似的,将整个舒家垄掩得严严实实。雾锁舒家垄。我和梦林还有些同学,也跟着打火的队伍,急冲冲地往舒家垄方向跑。进舒家垄的每条道路上,都有人向着发了火的舒家垄来。那时的乡村,老房多,木结构的房子多,因而火灾也多。只要村庄发火,去打火的人并不需要命令,而是有火人自来。这是一种乡间的约定俗成,也是一种乡间最古老的契约,还是乡村千年不变的哲学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。一时,进舒家垄的土路上,处处是嘈杂的脚步声,漫天的尘土飞扬。
天啊,是我家发火了。梦林还没到舒家垄,就尖叫一声,眼泪即刻瀑了出来。不会看错吧?我说。梦林打着哭腔回答道,怎么会呢?我家还能认错?也是啊,自己的家哪有不认识的呢?梦林加快了步伐,我跟在他后面,也不由得急切切地迈开脚步。到达舒家垄的屋前禾场时,梦林家的火已上了房顶,熊熊燃烧,能看见火苗在肆无忌惮地乱蹿,和他家连着的,梦林说是旺林家的,我感觉到那个叫旺林家的火势更猛。能听得见火烧干柴一般的“哔哔啪啪”声,和不时溅出的火星,像黑夜的星星;木板楼上的着了火的木板,拽着火苗急速下坠,像银河落九天似的。整个屋顶都烧穿了,黑漆漆的瓦就更黑了,破碎地散落在天井里,把天井几乎都覆盖了,一片狼藉。还有人冒着屋顶的火随时可能落下来的危险,在燃烧过的屋里穿进穿出,抢那些能够抢出来的东西。禾场上,已经堆着一些从家里抢出来的什物,棉絮棉被衣服和锅碗瓢盆什么的,一看就不值钱,但于生活来说,须臾不能或缺。还有几头猪被拴在禾场边的树上,哼哼唧唧。鸡们早已飞到了田畈,自由自在地觅食。而狗则围着着了火的屋堂,在禾场上狂吠。挨着那些破烂的旁边,有一张梳妆台,容易被人忽略。可我见了,像见着了一道闪电,令我眼睛一亮。“可怜楼上月徘徊,应照离人妆镜台”。这虽只是一张普通的梳妆台,但显然很有些年份,且做得颇为精致,尤其是镶镜子的边框,还雕有花饰,好像荷叶状,仿佛一株白莲荡漾在夏日湖面的清风里,飘来阵阵荷叶的清香。我猜想,将梳妆台抢出来的人,肯定是一位爱美之人。如果是位男人抢出来的,他一定很爱他的妻子;如果是位女人抢出来的,那她一定很美。即使不是貌美,也一定是心灵美。向往美,追求美,真是不分年月,不分时间,不分贫富,不分地域。
打火现场,被人围得水泄不通,叫唤声,脚步声,一片嘈杂。有高声喊的,有低声叫的:注意北面,切断火源;注意脚下,防止墙塌。而裹着三寸金莲的老娭毑,杵着龙头拐杖,站在禾场上,望着不熄的火焰,不停地在抹泪,喃喃地说,这可怎么得了,家全毁了。眼看冬天就要来了,这可怎么熬啊?说着又忍不住地掉着眼泪。童稚的孩子们懵懵懂懂,看见火苗,看见这么多的人,人来疯似的手舞足蹈。而更多的影像是:村里的男男女女和四面八方来支援的人们,排得像长龙一样,拿着五花八门的工具,一桶水、一盆水地在向前快速传递着,送到打火者手上。远处的水井边,两三位孔武有力的男人,轮番不停地用水桶在水井里汲水,并准确地倒进打火人员端着的密密麻麻的水桶和面盆里。然后,摆成长龙的打火人员一盆一桶地往发火的屋堂传送,有点像后来我们所见的工厂的流水线。汲水者,满身都是湿漉漉的,不知是汗还是水。后来,来参加打火的人太多,也有嫌流水线传递速度太慢的,便又开辟水源地,从远一点的水圳里取水,一桶一盆地输送到发火的地方。梦林和我也站进了传递水桶和面盆的队伍里了。
上屋脊是两把梯子捆在一起的长长的云梯。站在屋脊的每个不同方向,都有一位年轻的后生,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接过一桶或一盆水,拼命地往火势集中的地方泼。每一桶、每一盆水泼下去,火头就“滋”的一声,熄了哈,火苗就凹下去,但一倏忽,火苗就又蹿了上来。水和火,真是势不两立。它们就像两个拳击手,你一拳来,我一拳往,虽然彼此踉踉跄跄,步履蹒跚,但仍然僵持不下,此起彼伏。时而水占了上风,火苗就小一些,时而火占了上风,火苗就根本不在乎这一桶水一盆水的,仍然是迎风招展。后来,还是人多力量大,增加了在屋脊泼水的人,水,源源不断地输送,集中泼于火头,最终,舒家垄的这场大火被扑灭了。高高的马头墙,在防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将火势集中在梦林和旺林家,而没有越过山墙进而影响整个屋堂。只是梦林和旺林家损失惨重。梦林家的墙塌了一半,而旺林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,整个屋全圮塌了。
那个冬天,梦林和旺林家是怎么度过来的?在外搭个棚?还是借他人一间半室?我没问过梦林,就不得而知。但从梦林后来身上穿了崭新的黑色棉衣和棉裤看,我就知道,那是政府救济的标志。如果不是天灾,只有村里的五保户才有资格获得这种黑色的棉衣棉裤。突然想,怎么没有看到过其他季节的救济衣物呢?不会是没有吧?
前些天,隔着时空,在微信里和梦林聊天,我问他,还记得舒家垄的那次发火不?
他说,哪能不记得?是自己家啊。那时的村庄经常发火,全都是靠人在屋脊泼水。好在人心齐,只要哪家发火,附近周围村庄的人们都会拼了命去救,没有半点私心,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条龙的救火队伍。
我说,能感受到那时乡村的团结。
梦林又说,打火其实是件蛮危险的事,有时,一阵大风吹过来,火势冲天而起,站在屋脊打头灭火的年轻人,轻则头发眉毛衣服被烧着,重则不小心掉下房顶,会砸着楼梯上传送水的一排人,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,不幸摔死的也有。最危险的是,一不小心落到火海中,非死既残……乡下的村落每年都有火灾发生,有时候还不止一次,因打火而丧生的也不少。
哦,这可是我不知道的,还这危险啊。我回答道。
梦林继续说,火被打熄了,打火的队伍都悄无声息地各自回去了。没有人说报酬什么的,但条件好一点的失火主家,如果火灾不是太严重,受损失也少,一般会在一段时间后,杀头猪,请帮忙打火的人来家里打个牙祭,以示犒劳;如果家庭条件不怎么好的,火灾损失又严重,自救都还来不及的,也就没能力回请大家了。但大家也没有埋怨,表示充分的理解。下次哪里再发了火,大家照样会全心全意尽力去打火。
我听了,惊叹:噢,还有这多礼在其间啊!
说完这,梦林感叹地说,现在,村庄的老屋几乎都破败了,重建时也都改成了水泥钢筋平顶屋或楼房。屋或楼,漂是漂亮了,但再也找不回那种幽静岁月、民风淳朴的味道了。而今,村子里也不再发火了,即使发了火,也没有人去救了。年轻人都进了城,空心村比比皆是,即便好一点的村庄,也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和失怙的孩童。连老(鄂南方言:死)了人,抬上山的殇夫都难得找。哪还能凑得齐那打火的长龙?
我接过梦林的话说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今日村庄的凋敝,倒不是说房子和路,现在村子里的房子比任何时候都新,村村通都是簇新的水泥路,连水塘都镶上了汉白玉栏杆,而是说维系乡村鲜活的魂和精气神,在逐渐失落。
梦林深深地认同,说,再想想当年的那打火的场面,其实是蛮感动人的。
所以,乡村振兴迫在眉睫。
崇阳多山,俗称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东北部的田心黑桥的两山之间,有一垄平畴,除了弯弯曲曲的田塍围着的水田外,还有一处像浮在田间的岛屿一样的屋堂,和众多的鄂南民居一样,也是屋连着屋,廊连着廊,甬道连着甬道,天井连着天井;而屋里的内饰多为木制品,包括门板、桌椅、木柜、雕花窗和床;只有高高的山墙,翘出飞檐,隔着每片屋宇,也是一道防火墙。屋宇上,鱼鳞般的黑瓦,一摞一摞地排列,瓦沟深幽,长满青苔,透着沧桑。因屋堂的人大多姓舒,便有了舒家垄这个名称。舒家垄离我们读书的黑桥小学不远,十几分钟就能到。下课后,站到操场上,一眼就能望到舒家垄的俨然房舍和在农田里耕作的农人。
火苗,隔老远就能看到像蛇信子一般的火苗在往上蹿。紧接着是巨大的浓烟,像烽火台的狼烟似的,将整个舒家垄掩得严严实实。雾锁舒家垄。我和梦林还有些同学,也跟着打火的队伍,急冲冲地往舒家垄方向跑。进舒家垄的每条道路上,都有人向着发了火的舒家垄来。那时的乡村,老房多,木结构的房子多,因而火灾也多。只要村庄发火,去打火的人并不需要命令,而是有火人自来。这是一种乡间的约定俗成,也是一种乡间最古老的契约,还是乡村千年不变的哲学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。一时,进舒家垄的土路上,处处是嘈杂的脚步声,漫天的尘土飞扬。
天啊,是我家发火了。梦林还没到舒家垄,就尖叫一声,眼泪即刻瀑了出来。不会看错吧?我说。梦林打着哭腔回答道,怎么会呢?我家还能认错?也是啊,自己的家哪有不认识的呢?梦林加快了步伐,我跟在他后面,也不由得急切切地迈开脚步。到达舒家垄的屋前禾场时,梦林家的火已上了房顶,熊熊燃烧,能看见火苗在肆无忌惮地乱蹿,和他家连着的,梦林说是旺林家的,我感觉到那个叫旺林家的火势更猛。能听得见火烧干柴一般的“哔哔啪啪”声,和不时溅出的火星,像黑夜的星星;木板楼上的着了火的木板,拽着火苗急速下坠,像银河落九天似的。整个屋顶都烧穿了,黑漆漆的瓦就更黑了,破碎地散落在天井里,把天井几乎都覆盖了,一片狼藉。还有人冒着屋顶的火随时可能落下来的危险,在燃烧过的屋里穿进穿出,抢那些能够抢出来的东西。禾场上,已经堆着一些从家里抢出来的什物,棉絮棉被衣服和锅碗瓢盆什么的,一看就不值钱,但于生活来说,须臾不能或缺。还有几头猪被拴在禾场边的树上,哼哼唧唧。鸡们早已飞到了田畈,自由自在地觅食。而狗则围着着了火的屋堂,在禾场上狂吠。挨着那些破烂的旁边,有一张梳妆台,容易被人忽略。可我见了,像见着了一道闪电,令我眼睛一亮。“可怜楼上月徘徊,应照离人妆镜台”。这虽只是一张普通的梳妆台,但显然很有些年份,且做得颇为精致,尤其是镶镜子的边框,还雕有花饰,好像荷叶状,仿佛一株白莲荡漾在夏日湖面的清风里,飘来阵阵荷叶的清香。我猜想,将梳妆台抢出来的人,肯定是一位爱美之人。如果是位男人抢出来的,他一定很爱他的妻子;如果是位女人抢出来的,那她一定很美。即使不是貌美,也一定是心灵美。向往美,追求美,真是不分年月,不分时间,不分贫富,不分地域。
打火现场,被人围得水泄不通,叫唤声,脚步声,一片嘈杂。有高声喊的,有低声叫的:注意北面,切断火源;注意脚下,防止墙塌。而裹着三寸金莲的老娭毑,杵着龙头拐杖,站在禾场上,望着不熄的火焰,不停地在抹泪,喃喃地说,这可怎么得了,家全毁了。眼看冬天就要来了,这可怎么熬啊?说着又忍不住地掉着眼泪。童稚的孩子们懵懵懂懂,看见火苗,看见这么多的人,人来疯似的手舞足蹈。而更多的影像是:村里的男男女女和四面八方来支援的人们,排得像长龙一样,拿着五花八门的工具,一桶水、一盆水地在向前快速传递着,送到打火者手上。远处的水井边,两三位孔武有力的男人,轮番不停地用水桶在水井里汲水,并准确地倒进打火人员端着的密密麻麻的水桶和面盆里。然后,摆成长龙的打火人员一盆一桶地往发火的屋堂传送,有点像后来我们所见的工厂的流水线。汲水者,满身都是湿漉漉的,不知是汗还是水。后来,来参加打火的人太多,也有嫌流水线传递速度太慢的,便又开辟水源地,从远一点的水圳里取水,一桶一盆地输送到发火的地方。梦林和我也站进了传递水桶和面盆的队伍里了。
上屋脊是两把梯子捆在一起的长长的云梯。站在屋脊的每个不同方向,都有一位年轻的后生,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接过一桶或一盆水,拼命地往火势集中的地方泼。每一桶、每一盆水泼下去,火头就“滋”的一声,熄了哈,火苗就凹下去,但一倏忽,火苗就又蹿了上来。水和火,真是势不两立。它们就像两个拳击手,你一拳来,我一拳往,虽然彼此踉踉跄跄,步履蹒跚,但仍然僵持不下,此起彼伏。时而水占了上风,火苗就小一些,时而火占了上风,火苗就根本不在乎这一桶水一盆水的,仍然是迎风招展。后来,还是人多力量大,增加了在屋脊泼水的人,水,源源不断地输送,集中泼于火头,最终,舒家垄的这场大火被扑灭了。高高的马头墙,在防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将火势集中在梦林和旺林家,而没有越过山墙进而影响整个屋堂。只是梦林和旺林家损失惨重。梦林家的墙塌了一半,而旺林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,整个屋全圮塌了。
那个冬天,梦林和旺林家是怎么度过来的?在外搭个棚?还是借他人一间半室?我没问过梦林,就不得而知。但从梦林后来身上穿了崭新的黑色棉衣和棉裤看,我就知道,那是政府救济的标志。如果不是天灾,只有村里的五保户才有资格获得这种黑色的棉衣棉裤。突然想,怎么没有看到过其他季节的救济衣物呢?不会是没有吧?
前些天,隔着时空,在微信里和梦林聊天,我问他,还记得舒家垄的那次发火不?
他说,哪能不记得?是自己家啊。那时的村庄经常发火,全都是靠人在屋脊泼水。好在人心齐,只要哪家发火,附近周围村庄的人们都会拼了命去救,没有半点私心,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条龙的救火队伍。
我说,能感受到那时乡村的团结。
梦林又说,打火其实是件蛮危险的事,有时,一阵大风吹过来,火势冲天而起,站在屋脊打头灭火的年轻人,轻则头发眉毛衣服被烧着,重则不小心掉下房顶,会砸着楼梯上传送水的一排人,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,不幸摔死的也有。最危险的是,一不小心落到火海中,非死既残……乡下的村落每年都有火灾发生,有时候还不止一次,因打火而丧生的也不少。
哦,这可是我不知道的,还这危险啊。我回答道。
梦林继续说,火被打熄了,打火的队伍都悄无声息地各自回去了。没有人说报酬什么的,但条件好一点的失火主家,如果火灾不是太严重,受损失也少,一般会在一段时间后,杀头猪,请帮忙打火的人来家里打个牙祭,以示犒劳;如果家庭条件不怎么好的,火灾损失又严重,自救都还来不及的,也就没能力回请大家了。但大家也没有埋怨,表示充分的理解。下次哪里再发了火,大家照样会全心全意尽力去打火。
我听了,惊叹:噢,还有这多礼在其间啊!
说完这,梦林感叹地说,现在,村庄的老屋几乎都破败了,重建时也都改成了水泥钢筋平顶屋或楼房。屋或楼,漂是漂亮了,但再也找不回那种幽静岁月、民风淳朴的味道了。而今,村子里也不再发火了,即使发了火,也没有人去救了。年轻人都进了城,空心村比比皆是,即便好一点的村庄,也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和失怙的孩童。连老(鄂南方言:死)了人,抬上山的殇夫都难得找。哪还能凑得齐那打火的长龙?
我接过梦林的话说,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今日村庄的凋敝,倒不是说房子和路,现在村子里的房子比任何时候都新,村村通都是簇新的水泥路,连水塘都镶上了汉白玉栏杆,而是说维系乡村鲜活的魂和精气神,在逐渐失落。
梦林深深地认同,说,再想想当年的那打火的场面,其实是蛮感动人的。
所以,乡村振兴迫在眉睫。